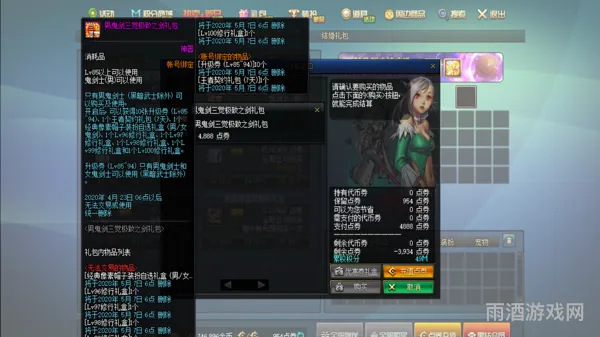明朝时代紫薇套装
定陵共出土绶两组,形制和式样完全相同,每组含两条小绶和一条大绶,大绶和小绶都用红、黑、绿、黄、白五色丝线编织而成,大体形制符合制度记载,但所用丝线和制度规定有出入,且大绶上没有发现应有的玉环

但不管是文字制度还是图画,都与定陵出土的黄裳残片有较大出入,所以较难推测嘉靖八年制的黄裳具体形制,但是参考同时期明世宗对官员朝服的要求也与六章黄裳的要求相近,朝服下裳多了一条“每幅作三襞积”的要求,笔者推测或许真实的黄裳和嘉靖改制后的朝服下裳的结构相似
搭配衮冕所用的鞋子,洪武二十四年定制,红色布料制成,鞋间装饰有云头,云头用金*缘边,脚背处位置用黑色丝绦系紧固定(“黄条缘玄缨结”),穿戴赤舃时内部还要穿以朱袜(红色的袜子)
“有二小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三小绶,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龙文,皆织成。”
衮冕配件之一,是用于遮挡腰部到下腿位置的衣物,嘉靖八年制度要求蔽膝用黄罗制成(“蔽膝随裳色”),尺寸规定上宽一尺,下宽二尺,长三尺,蔽膝边缘施以丝绳(紃),丝绳之内的部分绣龙纹一个,火纹三个,蔽膝用金钩系于革带之上
明朝时代装备一览表
嘉靖八年,明世宗要求冕服中重新加入革带(明制革带,皇帝应用*带鞓饰以玉片的玉革带),用于悬挂其他的冕服组件,但此革带与普通革带不同,应该是考虑到革带后面悬挂的大绶较为影响穿着的舒适性,所以革带后段并未装饰七块排方板,即记载中的“前用玉,其后无玉”
定陵出土黄裳的保存并不完善,原件已破败成残片,连完整的结构都难以分辨,但通过专家绘制的定陵黄裳图仍然可看出与嘉靖八年制度的出入,如正裙门和另外绣有章纹的裙门之间有两片褶子,正裙门两边的褶子和三个裙门构成了“七幅”中的“五幅”,其他两幅为带章纹裙门两边的数片褶子
同时,《定陵报告》中并未记录“黄绮”,只记录有随玉镇圭出土的三件玉圭垫,出土时垫在玉镇圭之下,《定陵报告》中所称的玉圭垫
衮冕作为明代皇帝、宗藩亲郡王的最高等级、出席一些大型祭祀和重要活动时所穿的礼服,于洪武元年(1368年)初制定,由于明初一系列礼制制定的尚不完善,后续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此不赘述,依据《大明集礼》《明宫冠服仪仗图》《大明会典》《三才图会》可知,明代皇帝衮冕的发展一共有以下几个阶段
绶用六色丝线编织而成,大绶形制为长方形,小绶形制为剑形,大绶上施加有六条“小绶”,“小绶”之间连结玉环(此物和身体两侧穿戴的小绶同名,注意不要混淆)
明朝时代手机可以玩吗
依据《定陵报告》,定陵中出土两件大带,形制和样式基本相同,大带上长58公分,下垂部分长29公分,形制与制度记载基本符合,但具体细节有出入,如大带两端各钉有三条用于系紧固定的金色绸带(两端合共六条),大带的内外都用红褐色罗制成,并非记载中的“素表朱里”,且上下部分均为红罗缘边,同时两端搭配有青色的丝绦
除此副玉佩外,还有两副玉饰件形状、细节完全相同的玉佩,通长约50公分(只有成年男子腰部到膝盖位置的长度),不同的玉饰件上分刻有正龙纹和金花卷云纹,该类玉佩大体形制符合制度记载,仅有一项出入,即该玉佩在玉花和玉滴之间又有一排和玉瑀和玉琚相同的玉饰件,《定陵报告》认定该两副玉佩属于两皇后,笔者推测两副玉佩应该都属于万历帝,一副为搭配衮冕,另一副搭配皮弁冠服
根据《定陵报告》,定陵共出土七副玉佩(含皇后所用玉禁步),其中一副为标准形制的礼服用玉佩,穿以金色丝线,所饰玉饰件的排布、数量完全符合制度,通长约55公分,不同的玉饰件上分刻有牡丹花纹和云凤纹,与制度记载出入,《定陵报告》认定该玉佩属于万历帝,笔者认为不然,由玉饰件上的纹样推断,该副玉佩应当为万历帝原配皇后所用。
嘉靖八年(1529年),明世宗朱厚熜重新更定一系列礼仪服饰制度,皇帝衮冕形成明代最终款式,1956年,明定陵发掘工程启动,其中便出头有陪葬的衮冕实物,本文依据万历本《大明会典》(下文简称为《会典》)和《明定陵考古发掘报告》(下文简称为《定陵报告》)以嘉靖八年制皇帝衮冕为参照和明定陵出土实物探究明后期皇帝衮冕的形制结构
作为束腰所用的礼服大带,嘉靖八年制度与明前期制度并无较大差异,大带用罗制成,有下垂部分,外用白色罗,内用红色罗(即记载中的“素表朱里”),大带上部分饰以红罗缘边,下垂部分饰以绿罗缘边,穿着时两端用纽扣固定相连(即记载中的“纽约”),缀以素白色丝绦(即记载中的“用素组(素白色组带)”)
标签: #定陵报告